【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在失眠时“数羊”?这位学者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走近狐狸、刺猬、蝾螈、甲虫、猎犬,甚至“海怪”,讲述它们与这片土地之间不为人知的历史纠葛。
你的心里有没有一只特别的动物?它可以是你童年时的好伙伴,也可以是想象中的好朋友。一只任你打扮的好脾气猫咪?一条听你召唤就能飞进卧室的龙?又或者是河边那群表面优雅、实则凶猛的天鹅?只要认真回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藏着一段与动物有关的“野性往事”。英伦诸岛也不例外。
《野性英伦》是一本从动物视角重新讲述英国历史的书。作者凯伦·R·琼斯是肯特大学的环境史学家。在她看来,过去的历史写作往往只聚焦人类,并常常忽视我们的祖先与其他物种的日常互动。当我们选择从“野性视角”看待过去时,会发现动物无处不在:河狸在时尚史中“啃”出一条路(它们的毛皮曾是制帽原料),猎隼在中世纪的徽章中翱翔,毛驴在夏日的海滨上高声嘶叫……从冰河时代到机械时代,从黑死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历史的各大转折时刻因为“野性”的加入而生动起来。
那么,要怎样去书写“动物的历史”呢?历史学家埃丽卡·法奇曾说,所谓“动物史”,其实就是人类如何看待其他物种的历史。毕竟,我们既听不懂夜莺或蟾蜍的叫声,也没有獾或鲨鱼的日记可看。因此,用动物自己的声音讲述它们的故事是不可能的。但幸运的是,历史的记录中处处都有动物留下的痕迹:法律、诗歌、文学……动物出现在中世纪手抄本的书页上,出现在士兵日记本的素描图里,也藏在业余博物学家的笔记本中。通过这些材料,借助考古、卫星定位、科学研究报告与DNA痕迹,琼斯试着还原出一段“动物的历史”。
当人们看到一只狐狸、刺猬或猎犬时,脑海中浮现的不仅仅是它们的真实模样,还会有我们从小读过的童话故事、翻过的百科全书、看过的儿童节目所留下的“先入为主”的印象。
而这种“预设认知”会对某个物种的命运造成深远影响。以刺猬为例:琼斯在书中写道,刺猬已经在不列颠群岛生活了1500万年,它们见证了猛犸象的灭绝,也见证了第一批人类抵达欧洲。人类到来之后,刺猬们逐渐背上了“邪恶”的名声。有人说它们会在夜间潜入村庄偷吃鸡蛋(这是真的),甚至吸吮沉睡乳牛的奶水(几乎可以肯定是假的)。它们能够啃食有毒的蟾蜍而不中毒(这是真的),传说中还能在女巫丢失扫帚后充当“坐骑”(听起来就很扎)。这些说法共同构建了一种“黑化”的刺猬形象,于是捕杀刺猬成了“为民除害”。英格兰柴郡一个村庄的记录显示,在17世纪末期,当地人在35年间共猎杀了8585只刺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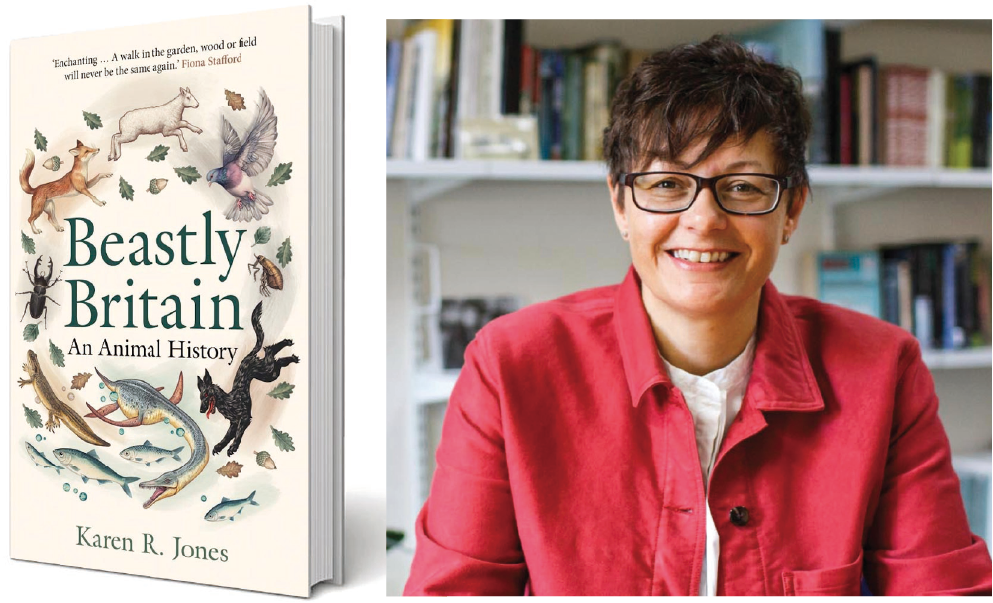
左图为《野性英伦》,右图为本书作者凯伦·R·琼斯。(图片来源:耶鲁大学出版社/肯特大学官网)
这与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如今的刺猬可谓英国民众的“心头好”,常年位居“最受欢迎动物”排行榜前列。人们在自家花园里为它们搭建庇护所,还担心它们过马路时的安危。琼斯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彻底转变可以追溯到一本深受喜爱的童书——“彼得兔”系列童书作者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刺猬温迪琪的故事》。在这本1905年出版的经典童书中,温迪琪太太是一只拟人化的刺猬,职业是洗衣妇。她细心打理邻居们的衣物,包括彼得兔那件标志性的蓝色小外套。这本书让刺猬的形象从过去的“捣蛋鬼”转变为“可爱帮手”,影响深远。1983年成立的一家刺猬救助慈善机构就以“温迪琪”命名,如今该机构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野生动物医院。
《野性英伦》这本书里充满了这样的故事。琼斯聚焦于人们身边常见的动物,比如蝾螈、刺猬、鸽子、绵羊、跳蚤等。她既描绘它们的生物学特性,比如打洞、飞行、繁殖等行为,也追踪它们在文化记忆中留下的印记——它们被人类赋予怎样的象征意义,为什么会被喜欢、被误解,甚至被恐惧。
书中指出,人类对动物的“文化想象”常常与实际的“自然知识”发生出人意料的碰撞。就拿绵羊来说,它们通常被视为“乡村背景音”,平凡无奇、咩咩叫着,唯一的作用似乎是助你入眠。但实际上,琼斯告诉读者,它们非常聪明,能识别多达50只“羊朋友”的面孔,还能记住照顾它们的人类。
《卫报》书评称,本书不断带来令人惊奇的新发现,比如我们其实还生活在恐龙的“后代”之中。下次当一只鸽子飞下来抢你手里的炸薯条时,不妨仔细观察它那带有鳞片、像爬行动物一样的脚——那是源自“始祖鸟”的遗传特征。始祖鸟是一种有翅膀、体型和乌鸦差不多的恐龙,长着骨质尾巴和飞羽,能短距离滑翔。不过,《野性英伦》里最引人遐想的,是一个听上去更不可思议的猜测:在英国德文郡和康沃尔的海岸外,或许仍有一群蛇颈龙(古代海洋爬行动物)在水中游弋。否则,如何解释那么多目击报告提到有人在海上看到一种巨大的、脖子很长、脑袋像蛇、长着吓人獠牙的灰色“海怪”?理智告诉我们,这些所谓“海怪”很可能只是翻身的鲨鱼,或者海上漂浮的大块垃圾;但内心那部分爱幻想的我们,却更愿意相信它们是史前时代的遗存。正如琼斯所说,那是一种“身边的异兽”——仿佛近在咫尺,却始终无法看清真面目的神秘存在。
(编辑:唐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