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在欧洲历史上,很少有比1848年春天更激动人心或令人恐惧的时刻。像变魔术一样,从巴勒莫到巴黎再到威尼斯,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人们聚集在一起,或采取和平手段,或采用暴力手段,拿破仑倒台后维持了数十年的政治秩序就这样崩溃了。
“我们正站在欧洲命运的转折点上。”1848年2月,普鲁士外交官约瑟夫·冯·拉多维兹警告说。这一年,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蔓延。1月,西西里岛爆发了反对波旁王朝国王费迪南多二世的叛乱。六周后,巴黎的一场叛乱推翻了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到了3月,革命的火焰已经吞噬了从米兰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布达佩斯的各个城市。
《卫报》书评指出,1848年的一系列革命在欧洲史学界占据着不寻常的位置。大多数历史学家承认它们作为欧洲范围内一系列起义行为的重要性。然而,在很多欧洲人的意识中,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淹没的存在,与其说它们是拉多维茨口中的“命运转折点”,不如说是英国历史学家特里维廉眼里“现代历史未能转向的转折点”。
《革命之春》是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关于这一系列革命的一部精彩历史著作,它挑战了特里维廉的判断,试图重塑人们对1848年的理解。
克拉克反对历史学家们关于“起义失败”的共识,认为只谈论“成功”和“失败”是忽略了问题的关键。他坚信,应该根据起义的影响来判断起义的意义,而在他看来,1848年留给后世的遗产是巨大的。
书的一开头,他就详尽描述了革命发生的物质背景:大量欧洲民众“经济不稳定”,被饥饿和瘟疫蹂躏,受到贪婪和不道德的雇主、地主和统治者压迫。不过,革命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状况不满的产物。他认为,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推动了叛乱的发生。
在叙事中,克拉克出色地将无数条线索编织在一起,使读者能够看到事件的细枝末节,以及欧洲范围内的综合视野。虽然不同国家的革命接踵而至,但并不是一个国家的起义成为下一个国家的导火索。相反,所有起义行动都是由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催生的,这些条件跨越了整个欧洲大陆,因为它们“植根于相同的、互相联系的经济空间,在相似的文化和政治秩序中展开”。
这些起义最初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带来了新议会、新自由和新宪法。但在一年之内,旧秩序开始卷土重来,而且往往非常凶猛,许多新获得的政治和社会自由被收回了。克拉克认为,这是因为革命者无法建立足够强大的国际团结力量,以抵御“反革命国际联盟带来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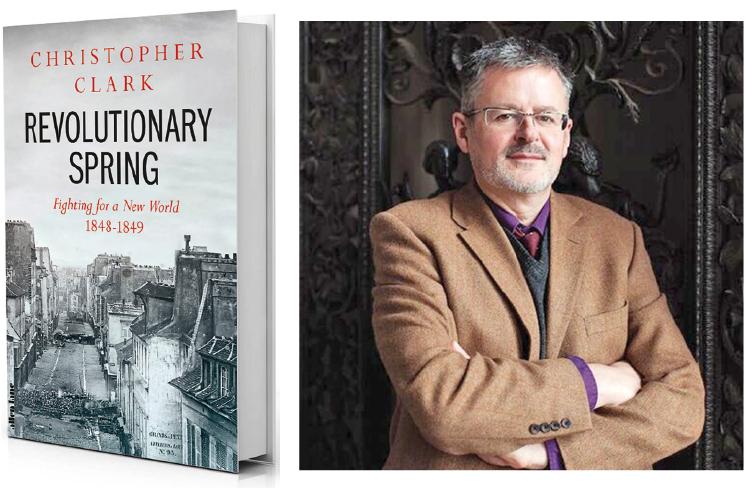
左图为《革命之春》,右图为本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图片来源:企鹅图书/剑桥大学官网)
贯穿《革命之春》一书的最重要线索,也许是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两个群体之间频繁的公开冲突。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含义尚未完全成形,而1848年在帮助划分这两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由主义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作家、思想家和政客们,他们认为自己被困在“革命与专制”之间,希望在传统统治秩序的特权和等级制度与他们所认为的激进派独裁主义和社会极端主义(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克拉克认为,自由主义者在肯定“财富特权”的同时拒绝“出身特权”,要求“政治平等”而不坚持“社会平等”,主张“人民主权”的原则,同时也限制这种主权,以免它危及自由。他们不是民主人士,因为虽然他们“渴望为人民说话”,但他们真正所指的“人民”只是“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男性纳税人”。他们充其量是“勉强的革命者”。
激进主义的定义则更为模糊,它是一种从乌托邦主义到刚萌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哲学的结合体。激进派的立场主要体现在“社会问题”上,也就是改善工人阶级和穷人所面临的不堪状况,从而产生了对工作权、最低工资、物价管控的要求。自由派更注重政治自由问题,如选举权的范围、新闻自由、性别平等、废除奴隶制和解放犹太人。激进派将社会问题置于辩论的最前沿,在政治问题上往往比自由派走得更远,许多人要求普选权、更大的新闻自由度和更广泛的民主形式。他们还更愿意使用武力和暴力来改变政治格局。
《卫报》指出,虽然克拉克对这些辩论进行了全面的评估,但从书中能看出他更同情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这导致他淡化了自由主义者们在1848年社会动荡中的“黑化”程度——他们开始相信,需要保护社会不受“危险阶层”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皮克所言,悲观主义开始“殖民”自由主义。
克拉克的上一本书《梦游者》如今被视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决定性叙事。《革命之春》也可能会在关于1848年的讨论中占据类似的位置。
(编辑:唐快哉)

